国庆间,我们读《论语》,已经读到了《雍也第六》,孔子开始讲到颜回。温婷之前好像对孔子与他的弟子不是特别熟悉,但读了几个星期《论语》,也觉得颜回好像在孔子弟子的群体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。
在上一篇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,子贡讲到颜回时,讲颜回“闻一知十”,孔子也觉得自己不如颜回,“弗如也,吾与女弗如也”。蔡老师回应讲,孔子与颜回的师生关系非常优美。老师能够自叹不如弟子,而弟子的存在更加衬托老师伟大的人格。蔡老师讲,《论语》之优美,就在于孔子通过他与学生群体的对话,生动地刻画了一幅幅生意盎然的生命场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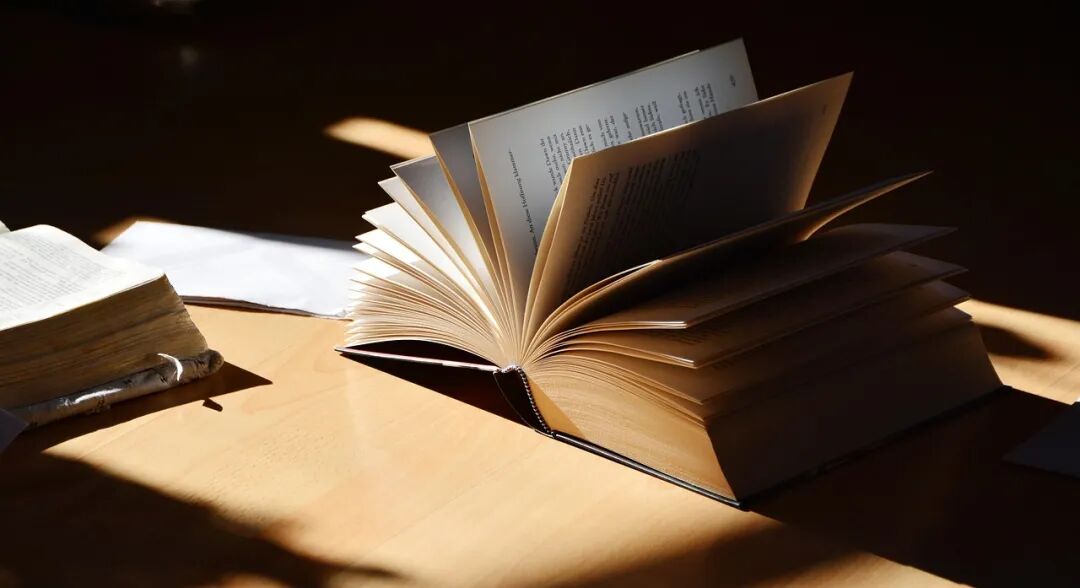
《雍也第六》这篇,孔子讲到颜回,“贤哉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。即使生活条件极其简朴,颜回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快乐和满足。回溯《学而第一》篇中,子贡讲到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”时,孔子讲,“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”。孔子所倡导的安贫乐道,现实中是可以做得到的。
这一篇有个有意思的地方,就是孔子讲颜回的时候也有一段:“回也,其心三月不违仁;其余,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孔子认为:仁不是一种外在表现,而是一颗心的恒常状态。颜回能做到“心里”没有一丝背离仁的念头。颜回不是偶尔闪现仁的火花,而是他的那团火能一直烧下去,不熄不灭、不冒烟、不摇曳,恒定而温暖。
孔子希望学生把“仁”当成一种心理常态,而不是偶发的道德行为。别人可以做出来仁,颜回是活成了仁的样子。一旦心里能长期“不违仁”,所有的礼、乐、言、行都会自带分寸与温度,中庸,庸常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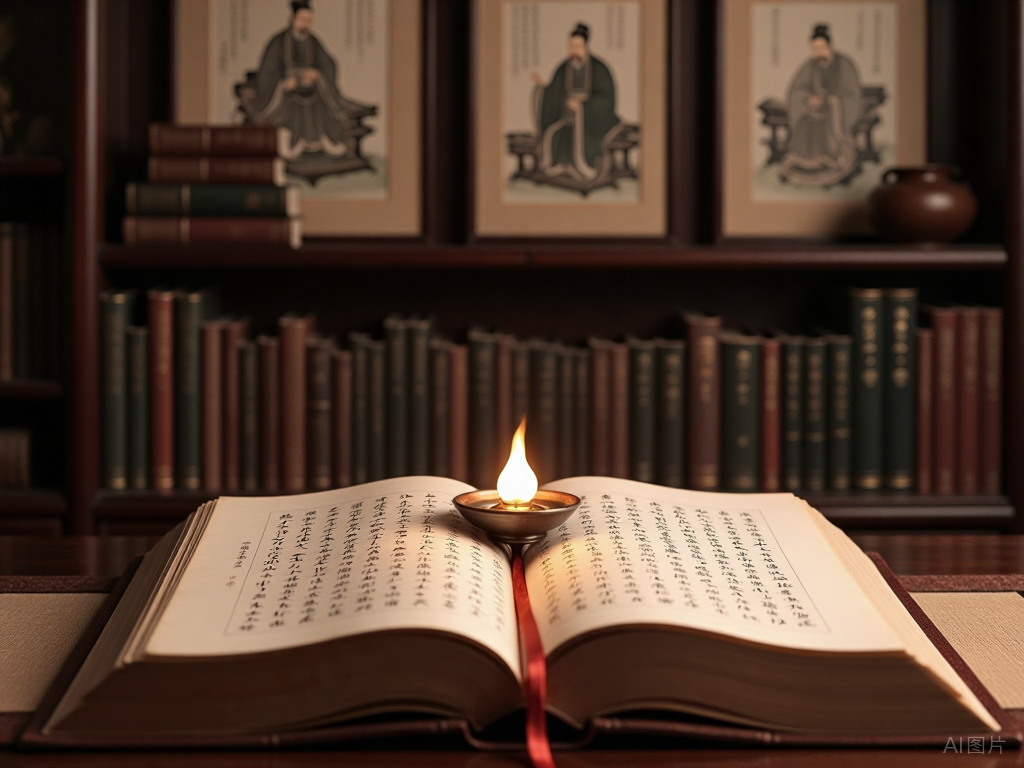
但在另一节中,也有“知者乐,仁者寿”的说法。那既然颜回仁,本来就应当寿,为何又“不幸短命死矣”?所以孔子是不是也有感叹命运无常的无奈,“天丧予!天丧予!”“亡之,命矣夫!斯人也,而有斯疾也!斯人也,而有斯疾也!”
颜回之死是否让孔子把“仁”与“寿”解绑,接纳“仁寿不齐”事实?后来孟子更讲“夭寿不贰,修身以俟之,所以立命也。”“不知生焉知死”,儒家把对于生命的体验、理解与修身立命,看做比生命本身更加重要。
从颜回之死看儒家的仁,更加讲内在、更自足、更坦然面对死亡。儒家没有“杀身成仁”的亢奋,也没有“死后天堂”的补偿,而是在不可知中坚持可知的生命追求,理解了仁赋予的生命意义,本身就是“寿”。
没有了道德热血,没有了烈士美学,儒家“有惧而无憾”。在我们认清生活真相后,依然热爱生活,依然追求理想,这应当是孔子对于生命无常认知以后所带来的一种观念,属于中国人对于生命的不同审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