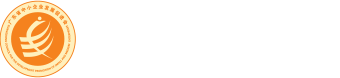一周时间,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组团企业家考察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。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,华人众多,各种口味的中餐馆林立,吃香喝辣。就连近年刚在顺德热火起来的海鲜桑拿蒸汽做法,吉隆坡餐厅也流行。
吉隆坡有一种鱼,称顺壳鱼,一般都有几斤重,大的有十来斤,淡水野生的,口味非常鲜美。跟广东的笋壳鱼同属于一个物种,学名为尖塘鳢。但其在形态和习性上差异很大,广东的笋壳鱼个体很小,味道远没有马来西亚的好。
《晏子春秋》: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,叶徒相似,其实味不同。所以然者何?水土异也。”
说起东南亚的华人,福建人、广东潮汕人最为熟悉。基本上,福建人、广东潮汕人家家户户都有亲族在东南亚。福建人多在马来与印尼,潮汕人多在泰国。
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,所谓的南洋,就是很多中国人的避难所与谋生之地。
其实,没有下南洋,只有南洋谋生。什么是下南洋,仅是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中心大国的一种观念。
在历史上,中国一直是一个大陆国家,对于海洋的认识和利用相对较少。而在明、清时期,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,以及对于海外贸易和移民的需求,中国的目光开始转向了海洋。中国移民大量涌向东南亚,寻求新的机会和发展。他们将中国视为自己的故乡,而将东南亚视为新的家园。下南洋的称呼也体现了中国移民对于故乡和家园的认知和情感。
中国下南洋有几个阶段,一是从郑和下西洋以后,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规模逐渐增大。在明朝时期,中国商人和水手开始向东南亚进发,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下来,成为了第一代海外移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移民到东南亚,包括从事贸易、开矿、农业和手工业等各个行业的人。
第二阶段是16、17世纪西方国家相继殖民东南亚国家以后,中国人主要作为劳动力而移居东南亚,跟随已定居海外的亲友赴东南亚学习做生意或从事劳工。
第三阶段,19世纪,是欧洲殖民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,也是世界大移民潮的开始。中国人于18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苦力谋生阶段,主要是太平天国、两广起义和广东土客大械斗等战乱的影响,中国东南地区满目疮痍,人们生活困苦而被迫出海。很多华人劳工是以“卖猪仔”方式被贩卖到东南亚种植园打工谋生的。但也有自由劳工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、手工业与农业活动的。
而今,接待我们的虽然都是华人,但文化已经略有不同。今天中国大陆发展了,但在我们大家的眼中,除了生意,还是生意。马来的华人,除了跟你谈生意,也还是谈生意。
毕竟而言,国家意识的形成、血缘的隔断、文化的割断,已经使全世界的华人对于中华的认知变得模糊。
不知道海外的华人,在全世界的发展,是谋生呢,还是生意。
然而,不管是橘还是枳,不管是笋壳鱼还是顺壳鱼,都是同一种物种。不管是大陆,还是东南亚,全世界的华人,都是同一种基因。变化虽有,但只要有链接,还能一脉相承,生生不息。
恰是在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,陈嘉庚号召华侨,出钱出力,支援中国抗战。三年时间,便筹得4亿国元,还招募了3000位华侨机工,在滇缅公路做司机、技工抢运物资。
这些华人机工有些中文都不会说,就凭家族长辈的一句话就回来了:是中国人,就必须报效祖国。来三千,留一千,死一千,回一千。他们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回国参战,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祖国,他们身上没有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,就是国家有难,平静尽责,再平静归来。
而今,中国也发展起来了,我们怎么看待今天的南洋,是生存,还是生意,还是生命延续中的生生不息?